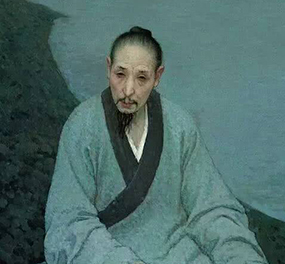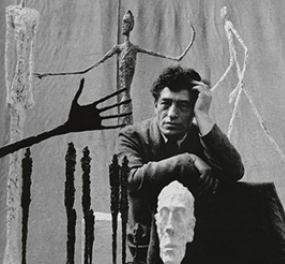|
仲星明談苗繡收藏: 我不收藏就被日本藏家收走了
蚩尤是中國的“戰神” 我收藏這些傳統的苗族藝術品已經30多年了,最初是出于對圖案的喜愛。我是學設計的,要研究圖案,在研究過程中發現,其他少數民族的刺繡,很大、很鮮艷,奪人眼球,唯獨苗族的刺繡大部分是大面積黑底或藍底,但是繡的內容細膩豐富,當時就對苗繡情有獨鐘。去了很多次黔東南地區,專門去考察。在收藏的同時我就在思考,圖案對他們的文化傳承究竟有怎樣的影響和作用?為什么會形成這樣的圖案和風格?為什么使用這樣的技法?慢慢發現,苗繡任何一個圖案,都有背后的歷史原因和文化脈絡,這就追尋到苗族人的祖先——蚩尤。 遠古的時候沒有文字,苗族的祖先是蚩尤,也是三皇五帝之一,他的子孫、族人要把他的故事記錄下來,就用圖案繡在衣服上面,穿在身上。傳說炎帝與蚩尤打仗,一下被打敗了,寸土不留。炎帝就去求助于黃帝,炎、黃兩族聯合起來攻打蚩尤,但是九戰九不勝,可見蚩尤的武力高強。如果中國歷史上要選一個“戰神”,那應該就是蚩尤。另外,他對農耕也有很大的促進。我們對蚩尤長久以來有誤解,我認為,現在的影視作品、動畫片都可以從這些歷史傳說故事中找到很多的創作靈感,多么的精彩。 不應把非遺傳承人“圈養起來” 現在很多刺繡技藝都已經失傳了。現在非遺傳承人的評選,是不是當地手藝最好的人得到這個榮譽?保護經費有沒有給最應該保護的人?保護方式是不是合理?我們看,這些老手藝是充滿生命力的,因為有信仰,是發自內心對神明的敬畏、對祖先崇敬、對子孫后代的愛。幾年、幾十年繡一件衣服,好幾代人傳承一件衣服。但是現在為了保護非遺,把手藝人召集起來,在景區里“圈養”表演作秀,這樣藝術的生命力就會慢慢喪失。非遺一定要活在它的源生地,有生活的需要,有生長的土壤。還有,現在很多培訓班,把非遺傳承人請到大專院校,給他們上專門的培訓課程,教藝術理論、教配色、教素描,“提高藝術修養”。這下好心做壞事,把老祖宗的“非遺”丟了,蚩尤教給他們的東西忘記了。這是文化上對民族傳統藝術的消解。 最最關鍵的是,創作時的“神性”沒有了。原來繡一件衣服是為了來年要去參加祭祀,帶有敬畏的心理,把圖案繡得非常精致,不敢怠慢的,但是現在這樣的祭祀活動少了,變成旅游的參觀項目,或者一種旅游商品,感情不同,結果完全不一樣。 我們要原汁原味地去保留屬于民族特有的藝術語言、文化精華。在這個基礎上,我們去尊重,去了解,去探索,解讀這種藝術語言的密碼,傳承幾千年的審美,有其中的道理。我呼吁,對少數民族的藝術一定要尊重,不要當作一般的藝術品,要當做“神品”,是帶有過去創作者的內心的信仰的。 “神品”不用批量 我最反對完全用數碼的手段做藝術作品,因為太過依賴數碼技術,會扼殺年輕人的原創能力。電腦、網絡確實很方便,但是也會造成人們依賴拷貝,有問題就去搜索,搜到就拿來用,沒有思考。因為這樣,我更加強調傳統,了解這些圖案中的內涵,才會知道怎樣去吸取其中的優秀的部分,為自己的創作提供靈感。要知道“非遺”的內涵才會真正尊重傳統文化。 現在市面上也有很多用機器做出來的刺繡,對于普及當地文化,宣傳旅游是有一定好處的。但是電腦繡,是千篇一律的,沒有感情,更不可能有鮮活的特色。我覺得少數民族的“神品”,不在于大批量的復制,比如像國際奢侈品牌,在包的設計上也只是使用了一點點的傳統元素裝飾一下,就有很高的價格。但是大批量的復制,反而只賣幾十塊,大批量的生產降低了其中的價值。
我的心愿是無償捐贈 我有緣收藏了黔東南地區十多面銅鼓。一個村子就只有一面鼓,只有在重要節日或重大祭祀活動的時候才會拿出來敲。銅鼓為什么是黑的,因為是埋在地底下的,活動結束后,族長會在銅鼓上刷上一層桐油,然后悄悄地把鼓埋起來,村里其他人都不知道埋在哪里,下一次活動再挖出來。就是怕被人偷走或賣掉。其實在二十幾年前收藏的時候我也很猶豫,因為我要是收藏了,村寨里就沒有了;但是我要不收,就被日本或是其他外國藏家收走了。所以我想,即使多出一些錢我也要收藏下來,這樣至少這些物品都還留在國內。 我已經收藏了幾百件苗族繡品了,我并不想占為己有,我一直有個心愿,想把這些藏品無償捐獻出來,希望這些苗繡精品能進相關博物館進行永久展示,讓更多的大眾認識苗繡和了解苗繡背后的文化故事,讓中國傳統苗繡文化得以永久傳承。 (仲星明,上海大學教授;本文由布彥特約采訪整理) 來源: 美術報 |